
11月11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,主力资金净流出883.67万元,占总成交额4.09%,游资资金净流入2056.13万元,占总成交额9.51%,散户资金净流出1172.45万元,占总成交额5.42%。
11月11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,主力资金净流出144.31万元,占总成交额1.51%,游资资金净流出38.23万元,占总成交额0.4%,散户资金净流入182.54万元,占总成交额1.91%。
12.1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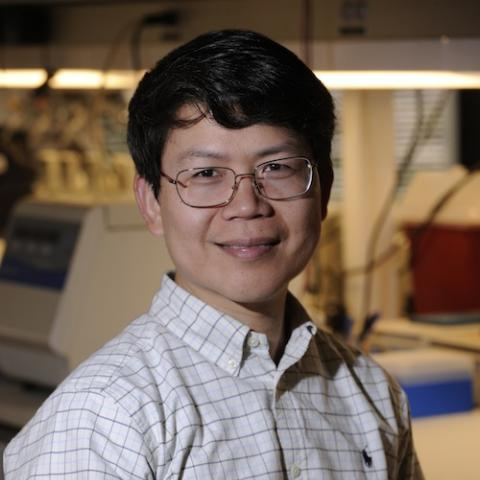
生物化学家,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,拉斯克奖得主陈志坚。图源: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官网
撰文 |严胜男 陈晓雪
● ● ●
对于陈志坚来说,从来就不存在第二条路。
从细胞转录因子NF-kB开始,到发现RNA传感中的MAVS蛋白,再到发现DNA传感中的cGAS酶,他一路从免疫信号通路的下游游到了上游,最后他解开了一个百年医学谜团:免疫系统如何知道自己何时受到攻击?
作为“早期反应者”,先天免疫系统必须快速识别外部入侵者和内部受损或死亡的细胞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免疫系统进化出了多种感知受体,每种受体在不同细胞类型中分布,能够识别特定的重复分子模式并触发相应的免疫反应。例如,Toll样受体(TLR)能够识别病毒、细菌、真菌和寄生虫特有的分子模式,而RIG-I样解旋酶家族则能够检测受感染细胞细胞质中的各种形式的病毒RNA。
能够检测异常DNA的传感器尤为重要,因为许多传染性病原体携带DNA,而所有细胞都含有DNA。在正常细胞中,DNA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和线粒体内;在受感染或死亡的细胞中,DNA可能会进入细胞质。长久以来,人们从未发现过一个真正的DNA受体。
直到2012年,陈志坚找到了它,一种在动物、细菌和微生物中都普遍存在的DNA传感器——cGAS。cGAS漂浮在细胞质中,一旦发现DNA入侵,便拉响警报,生成第二信使cGAMP,激活内质网中的STING蛋白(干扰素基因刺激剂)引发免疫反应。这一发现解释了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并应对病毒感染和DNA损伤。
2024年9月,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陈志坚被授予拉斯克奖(The Lasker Awards)基础医学研究奖,以表彰他发现“感知外来和自身DNA的cGAS酶,解开DNA如何刺激免疫和炎症反应的谜团”。拉斯克奖被誉为诺贝尔奖“风向标”,据统计已有86位拉斯克奖得主获得了诺贝尔奖。
几十年来免疫学领域不乏重大发现,但陈志坚始终专注在自己的这条路上。他是如何做到坚定地走唯一的路?这位从中国福建乡村走出来的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反过来发问,“如果你有自己的问题,你又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,为什么不把你的主要精力来追随你感兴趣、又认为很有意义的问题,而去追赶潮流?”
简单和坚韧是这位生物化学家的性格底色。在纯化cGAS酶过程中,他也曾感到束手无策,他们处理了 2000 多个细胞培养皿,纯化程度达到了 15000倍,但依然不足以将酶纯化到明显的同质性。摆在他面前有两种选择,放弃和再试试别的方法,他坚持了下来,提出了一种基于蛋白质纯化和定量质谱分析的混合方法。
他用一种“old fashion”式的生物化学的方式在这场寻找传感器的竞赛中胜出,它的竞争者是遗传学、系统生物学这些看似更先进的方式。
陈志坚说他自己直到博后出站都没有做到真正的科研入门,反而是在波士顿一家小公司一边科研一边做产品开发时,才真正了解什么样的问题重要,什么样的问题没那么重要。后来因为向往自由,31岁的陈志坚回到了学术界。在他的讲述中,实验的瓶颈、经费、终身教职、项目、文章,都不能称为一种苦和累。他说,“压力总是有的,不过,专注于工作,压力就会消散;工作没做好,压力就会累积”。
他从不花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,“Follow your observation,follow your interest”, 其他的事顺其自然。他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坚持的意义,“如果专注于某一个课题,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能比你对这个课题更懂的人不多。虽然有些实验室看上去很大,但真正和一个课题相关的可能就少数一两个学生或博后。如果你找到合适的课题并投身其中,你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实验室竞争”。
他永远被基础研究能发现的永恒时刻吸引,“它(cGAS)已经存在几十亿年,还很可能继续存在几万年或几亿年,发现这个永恒事物那一刻,本身就是激动人心的”。
11月5日,陈志坚被授予求是奖。知识分子专访了陈志坚教授,听他讲述自己的科研人生。
01
Old Fashion的胜出
知识分子:首先恭喜您获得今年的拉斯克奖,能不能先请您介绍一下cGAS发现的过程?
陈志坚:做cGAS或者DNA sensing(感知)之前,我们是做RNA sensing,就是说免疫系统怎么识别 RNA病毒,比如像流感病毒,丙肝病毒这样的免疫识别和信号传导的途径。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蛋白叫做MAVS,这是一个关键的蛋白。然后在MAVS的基础上,我们在上游和下游做了很多工作,前后也大概做了10年。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,就是DNA是怎么被识别的,特别是胞浆里面的DNA是怎么被识别的。原来我们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,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因为牵涉到很多细菌病毒,各种带DNA的病菌、微生物。另外一个也跟很多自身免疫疾病,包括癌症关系也很大。
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,发现竞争很厉害,有很多实验室都在做,他们也发表了不少文章。但是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个真正的 DNA的受体没有找到。
我们做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。前面有一个日本的博士后在做,有一些进展,但是关键的一步没有做出来。后来我们实验室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生化学家,叫孙立军,他来做这个体外的实验。他也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,才把试验给做出来。所以总共有花了4年左右的时间。
有很多实验室都在做,他们有一些人用系统生物学的手段,有一些人用遗传的手段,但是最后还是生化的手段成功了。
知识分子:其他人没有尝试用生化的手段吗?为什么其他人考虑了用遗传的手段或者系统生物学的手段,生化手段在当时会是最优的一个选择吗?
陈志坚:很多人认为生化的手段过时了,因为现在有了基因组,有了很多这种非常强大,非常有效的遗传筛选的手段。但其实我是不这么认为,我觉得传统的生物化学的手段还是非常有用,特别是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,比如说像质谱的技术,对我们做生化的人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。以前我们做纯化的时候要纯化很多蛋白,现在只要纯化一点点蛋白,就可以用质谱找到我们想要的蛋白,所以质谱技术给做传统生化的(研究者)带来非常大的帮助,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生化。生物化学就是follow activity,最后总可以找到东西,比如说蛋白或者别的分子,听上去是有点old fashion,但是既然有那么多成功的例子,几个非常重大的发现,原始的发现,都是通过生化的手段做出来的,为什么要抛弃这种有效的手段?
知识分子:从最初的NF-kB,到RNA传感MAVS再到DNA传感,您好像就这样一步步顺着免疫这条通道游到了上游来,这和其他的一些科学家还不太一样。有的人可能会同时布局两三个方向,用一个方向的研究去支撑另一个方向的研究,您当时是怎样想的,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忧?
陈志坚:我们倒是没有这个担忧,其实我们还是这是跟随我们的观察和发现,整个过程包括早期为什么会做ubiquitin(泛素),这都是由data来指导的,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,我们跟进,你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,然后又有新的现象。
我们也一般不去追赶潮流,在过去二十几年也有好几个非常热门的研究,比如说micro RNA,比如说到后面iPS细胞(诱导多能干细胞)等等。当然他们一些重要的技术手段我们也一直在用,包括基因编缉CRISPR-Cas9这些技术手段我们都在用。但是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碰到的问题去做。
知识分子: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到一个热点出现,会不由自主的就去进入到那个领域,您是如何去抵抗这种潮流?
陈志坚:如果说你有自己的问题,你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,并且认为它很有意义,为什么不把你的主要精力来做你感兴趣、又认为很有意义的问题,而去追赶潮流?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简单的。
知识分子:研究了这么久的免疫通路,最让您感到激动人心的环节是什么?
陈志坚:当然是我们发现cGAS的那一刻。就像我刚才说的,我们建立生化手段寻找DNA传感器,后来发现它是一个酶,能够催化合成一个全新的第二信使,这些都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。cGAS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,我们的团队是最早发现这样的分子机制的。我觉得做基础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,你发现的东西可能是永恒的,几千年、几万年后,这个东西可能仍然存在,所以这还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时刻。这种心情其实并不需要得到什么奖项才能感受到,当你发现的东西既有意思又重要,那一刻本身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的。
知识分子:做研究是技术重要,还是发现问题重要?
陈志坚:两个都重要,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更重要。发展技术的一个目的,其实也是要解决问题,就是看生物学里面有什么重要的问题。有了这个问题以后,这个时候就找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解决它,可以用生物化学的手段,可以用遗传学的手段,可以用细胞生物学的手段,各种各样的手段。有时候还需要开创一些新的技术才能解决提出来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有时候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些新的技术的开发,你一些技术比别人做得好,你可能就有优势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但如果真的要在两者之间来比的话,我觉得能够解决什么样生物学问题,才是最重要的。
02
要享受科研这个过程,
如果不享受的话那就不值得
知识分子:您是在什么时候您觉得自己可能最擅长的是做科学?从什么时候开始肯定了自己能够在这条路上可以继续走下去。
陈志坚:虽然读研究生时我也觉得科研挺有意思的,但感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入门。直到我在波士顿的一家小公司工作,那里我一半时间做科研,另一半时间参与产品开发,我才感觉自己真正入门了,能够独立开展工作,分辨出哪些问题重要,哪些不那么重要。在设计实验等方面,我也觉得自己算是开窍了。所以,相比其他人,我算是入门得比较晚。
知识分子:您曾经在产业界工作过一段时间,这样的经历在国内科学家里比较少见,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?
陈志坚: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原本没有考虑去公司工作。在做博士后期间,我帮助一个朋友推荐工作,之后对方提到还有一个职位空缺,问我是否感兴趣。当时我表示不感兴趣,因为我更倾向于去大学工作。但因为那家公司在圣地亚哥附近,离我所在的研究所只有一个小时车程,所以我决定去看一看。我发现公司的研究工作很有趣,特别是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名为T细胞治疗(car-t)的第一代研究项目,这让我感到兴奋。此外,公司提供的待遇对于博士后来说也很有吸引力。因此,我决定去公司工作。最终,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在公司工作了几年,分别体验了大公司和小公司。当时小公司的创始人是哈佛的教授,他们对做科研也很支持,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做科研,我那时候也发表了比较好的论文,为我重新回到大学打下了基础。
知识分子:您觉得您在产业界这段经历对于您去从事科研有什么样的影响吗?对选择研究问题会有帮助吗?为什么会回来,回来遇到哪些阻碍?
陈志坚:我想会有一些帮助。我们做科研的时候,总是下意识的会找一些跟疾病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一些课题。即使不是很有意的要去做一些跟疾病有关系的东西,但是下意识里面还是会往这方面靠拢的。
我回到学术界最主要是觉得学术界里面更自由一些,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,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。学校里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science,有cancer research,也有神经科学、发育生物学、微生物学,非常多样,所以学校的环境总的来说更适合科学创新。最后我选择到西南医学中心,我认为这里有最好的做科研的环境,有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。
知识分子:您刚刚回到学术界时在科研生涯起步阶段面临怎样的困难?
陈志坚:像所有助理教授一样,起初几年要申请项目、发表文章、招带学生,压力自然存在。但我当时更关注如何解决问题,而不是压力本身。压力总是有的,不过,专注于工作,压力就会消散;工作没做好,压力就会累积。
知识分子:当时没有这种压力,是不是跟您进高校时很年轻有关系,兜兜转转还是很年轻?
陈志坚:那时候也算是比较年轻。我回到学校成立实验室时31岁,开始自己的实验室是一件很激动人心的事情。我觉得更多的并不是压力,而是想着怎么把这个事情先做好。另一方面我当初也没有很大的野心,从来没有想过说会成为霍华德休斯研究员,更不敢想说会拿院士诸如此类的问题。就是把眼前的课题做好。第一步拿终身教职。
知识分子:是不是也跟您找到一个合适您做研究的环境有关,比如您可能跟国内目前大家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?
陈志坚:美国也有类似的要求,七年内要发表好文章、有基金的资助,才能获得终身教职。所有的助理教授都有一定的压力,但怎么去应对所谓的压力,我想大多数人也都是把事情做好,然后别的就顺其自然。
知识分子: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博士毕业生的增多,想要在高校寻求教职越来越难了,如何判断自己适合业界还是学界,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?
陈志坚:首先,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,如果你真的热爱科研,你才来做这件事情。其次,要判断自己是否擅长科研,这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入门,我在研究生阶段甚至到博士后阶段都还没有真正入门,直到我进入公司工作后,才感觉自己开始入门了。这同样需要时间来摸索。
最终,如果你既喜欢科研又能在其中做出新的发现,那么成为科学家或教授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事业选择。如果具备了这两点,所有问题,包括找工作的困难,都会迎刃而解。
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,有很多人跟我们说美国的教职很少,NIH的RO1项目资助率很低,只有百分之十几。如果整天去考虑这东西的话,我可能老早就不会走这一条道路,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还是傻一点好。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别的事顺其自然。工作做得好了,不是找不到工作,而是选择哪种工作,我知道很多做的好的博后都有多个工作机会。
特别是现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,有各种各样的声音,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影响。最后还是要静下心来问自己感兴趣的事是什么,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以后,然后你就去做,应该是可以做好。
知识分子:所以您也不会觉得,这个时代面对的问题会比您那个时代更艰巨或者是更严重?
陈志坚:是的,我觉得没有太大差别。每个时代都有其特点和挑战,比如八九十年代国内科研条件差,而现在条件好多了,但也面临新问题。无论如何,科研的本质没变,找到新发现总是值得欣慰的。回头看,如果你投入在自己热爱和擅长的领域,并有所收获,这就是成功。
知识分子:您从不觉得科研是一件特别苦的事情?
陈志坚:科研本身包括实验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。科研工作肯定不是朝九晚五就能完成的,有时一个实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,这是常有的事。但如果真正投入其中,其实并不会感到特别痛苦。即使现在我不再亲自在实验室做实验,我仍然花费大量时间阅读论文、撰写论文,这些工作虽然繁重,但我也不觉得痛苦。如果你真的热爱这项工作,即使在工作时间之外,比如回到家中阅读一篇优秀的论文或听一场精彩的研讨会,这也是你愿意主动去做的事情。这和你做其他任何令你享受的事情,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科研还是要享受这个过程,如果不享受的话,那就不值得,还有别的选择。
03
专注一个课题,
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实验室竞争
知识分子:哪些东西让您一步步走到现在?您觉得您做科研的特质是什么?
陈志坚:有一点点韧劲,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。一个就是说对做科研有兴趣,总会想着一些新的问题,还有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,会不断的去琢磨,然后不轻易放弃。
另外一个就是说搞科研还是需要很专心的去做这个事情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。
知识分子:现在如果让您对一些年轻的PI提一些建议,您会提什么建议?
陈志坚:如果你专注于某一个课题,你应该有信心,这个世界上没几个人能比你更懂这个课题。即便是在一些大实验室里,真正深入一个课题的可能也就一两个学生或博士后。所以,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课题并专注于它,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实验室竞争。
还有一点,PI在刚开始时还是要尽量亲自做实验。最初的这几年非常宝贵,你应该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江山,不能完全依赖学生或博士后来为你打江山。也不要丢了那些做实验的基本工具,尤其是在国内,年轻的PI一开始可能就会有很多学生,但这不一定是好事。还是要自己进入实验室,亲自做实验,带好学生。如果一个年轻的PI一下子有十几个学生,只做老板不做实验,还是有一定的风险。
知识分子:您能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分配时间的吗?
陈志坚:我大部分时间还是想科研的事情,因为别的也没有需要我们去想的。所以我觉得很幸运,可以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做科研上面。一般大概九点上班,晚上大概七八点钟左右回家,我的目标是7点前回家。
当然我现在出差也不少,就是说到外面去给讲座开会也不少。我是能够少旅行就尽量少旅行。这样子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实验室可以做一些事情,也可以跟实验室的人交流,跟他们一块就是分析数据,共同解决一些问题,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做,所以我希望是在这方面能够花更多的时间。
知识分子:做您的学生应该很幸福?
陈志坚: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亏欠他们的,还是应该多花一些时间给他们。
知识分子:论文的引用量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吗?
陈志坚:靠引用多少次并不完全说明问题。当然一篇文章被引用了几千次,这本身还是说明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有一定的影响。但一篇文章被引用5000次,也不见得就一定比引用1000次的好。所以一个科学发现,最后的影响力,还有它的重要性,还是要在领域里面,特别是同领域里面的专家来评更有意义,而不是完全靠这个引用率来评。
04
科学是最公道的
知识分子:cGAS-STING这条通路上,目前好像在STING上的药物研发会更多一点,cGAS上的转化会更少一点,cGAS的潜力是不是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到?
陈志坚:cGAS的抑制剂现在有很多公司都在研发。至于cGAS的激动剂,目前还不多,因为这涉及到如何激活酶的活性,这并不容易,但仍然是可行的。对于STING的激动剂,由于存在天然的分子可以激活STING,比如cGAMP是天然的STING激动剂,因此在cGAM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会相对容易一些。目前,抑制剂和激动剂两边都在同时进行研发。
药物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cGAS的发现时间还不长,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些时间。我在接受拉斯克奖采访时提到,GLP-1花了40年时间才成为一款神药,我们希望cGAS的药物研发不需要那么长时间,但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。
知识分子:目前的这条通路,您觉得还是有哪些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探索?
陈志坚:cGAS的调控非常关键,它既要能够应对各种微生物的感染,包括病毒、细菌和寄生虫,又要避免对自身DNA产生免疫反应。一旦cGAS被自身DNA激活,可能会引发多种炎症和自身免疫疾病,因此它的调控尤为重要,但这方面的调控机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究。至于STING的下游信号传导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。最近的研究热点之一是细菌中的cGAS,我们对它们是如何被激活的、具有哪些功能、有哪些不同的系统还知之甚少,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。
知识分子:您在美国已经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就,而且成为了美国科学院院士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华人里已经成为一个榜样?
陈志坚:我并没有这么觉得,我只是觉得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出了一些工作。是不是榜样我从来没有去往这方面想,但是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从我这个例子里面得到一些启发: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,或者有些人他可能就输在起跑线上,但是你只要是跟着你的兴趣去做,有一点点韧劲,最后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东西来的。
我个人觉得(做科学)有一个好处就是说,科学是最公道的,科学家总的来说还是看你所作出的贡献,你做的东西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受到同行的承认,不是靠一个人的社交技能可以改变的。我觉得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更注重事实,更注重数据,这是高于一切的,高于政治的东西,高于社交的东西。
比如说我们当初发现了cGAS以后炒股配资要求,最早认可我们工作的其实是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,因为一些外行的人他们也搞糊涂了:为什么发表了这么多DNA sensor(DNA感受器)。他们也搞糊涂了,不知道哪个是真。但是,我们同行里面的一些竞争对手,他们马上就知道这个是对的,马上就来祝贺我们。所以我想科学家是一群最尊重事实、最尊重数据的人。


